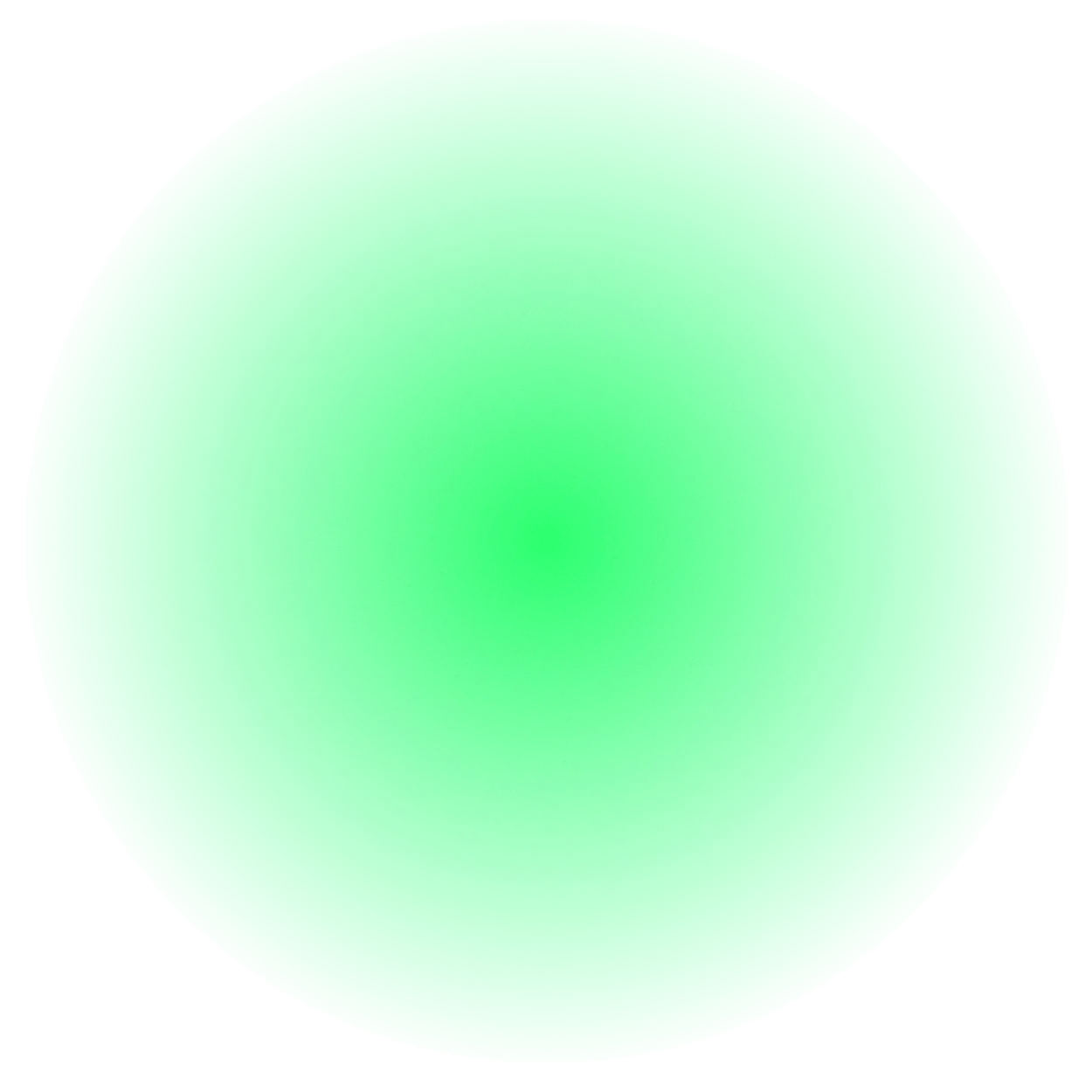click
您好,我是蔡崇隆,謝謝您來看這部讓人心情難受的紀錄片。自從九槍問世以來,我幾乎都會參加每場紀錄片的映後QA,希望直接面對觀眾的情緒和提問。不過因為9月1號上院線的場次過多,所以我改用文字的方式,跟您說明通常會分享的觀點和心情。
《九槍》這個片名似乎具有針對性,但其實是想讓觀眾顧名思義,能夠很快知道我們是從什麼事件出發。而在您看過之後應該也可以了解,阮國非事件雖然是本片的切入點,但是我們要思考的,是超越個案的結構性問題,甚至是台灣人面對東南亞移工的集體心理狀態。
我們常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我們以人情味和人權價值自豪,但似乎是隱含特定種族和階級為前提。我們並不覺得自己對東南亞移工有歧視,我也希望我們沒有,因為面對少數群體的態度,決定我們與極權國家的距離。我將《九槍》打造成一面投射移工議題的鏡子,可能也映照出台灣人不願意面對的實相。
但是《九槍》沒有想要控訴誰,只是希望藉著這個本來可以避免的悲劇,撐開一個台灣公民可以多元辯證的空間。畢竟悲劇已經發生了,只有難過或無力,並沒辦法改變什麼。
情緒沈澱之後,我希望片子可以帶給觀者一些正能量,大家在各自的社會位置上,利用本身的專業能力、資源或選票,為70萬名沒有話語權的移工處境啟動一些改變。
我也不斷呼籲,不要再用二元對立的視角來看待九槍事件。阮國非們淪為無證移工背後是不公義的制度及法令造成的,他有襲警和用藥的行為,即使罪不及死,也已經付出寶貴的生命,請不要再對死者加上任何負面標籤。
此外,陳姓員警違反用槍原則的部分,則已付出法律及職業生涯的沈重代價,他的家人說他原本是一個顧家上進,盡忠職守的年輕警察。他自己也曾表示,目前最大的壓力其實是來自大眾的輿論。
我認為事件雙方都是結構下的基層弱勢者。公民究責的方向應該指向不思改革的警政高層和制訂移工政策的政府官員,請不要重蹈覆徹誏弱勢者成為代罪羔羊。
最後,還是謝謝各位來看這部電影,雖然這個事件幾乎瓦解了我所相信的台灣價值,但是越來越多台灣公民對《九槍》的支持,讓我再度燃起強烈的信心。
我們每個人都希望成為更好的人,但不應該是踩在別人的身體上前進,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讓台灣成為一個真正民主共好的國家。
《九槍》這個片名似乎具有針對性,但其實是想讓觀眾顧名思義,能夠很快知道我們是從什麼事件出發。而在您看過之後應該也可以了解,阮國非事件雖然是本片的切入點,但是我們要思考的,是超越個案的結構性問題,甚至是台灣人面對東南亞移工的集體心理狀態。
我們常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我們以人情味和人權價值自豪,但似乎是隱含特定種族和階級為前提。我們並不覺得自己對東南亞移工有歧視,我也希望我們沒有,因為面對少數群體的態度,決定我們與極權國家的距離。我將《九槍》打造成一面投射移工議題的鏡子,可能也映照出台灣人不願意面對的實相。
但是《九槍》沒有想要控訴誰,只是希望藉著這個本來可以避免的悲劇,撐開一個台灣公民可以多元辯證的空間。畢竟悲劇已經發生了,只有難過或無力,並沒辦法改變什麼。
情緒沈澱之後,我希望片子可以帶給觀者一些正能量,大家在各自的社會位置上,利用本身的專業能力、資源或選票,為70萬名沒有話語權的移工處境啟動一些改變。
我也不斷呼籲,不要再用二元對立的視角來看待九槍事件。阮國非們淪為無證移工背後是不公義的制度及法令造成的,他有襲警和用藥的行為,即使罪不及死,也已經付出寶貴的生命,請不要再對死者加上任何負面標籤。
此外,陳姓員警違反用槍原則的部分,則已付出法律及職業生涯的沈重代價,他的家人說他原本是一個顧家上進,盡忠職守的年輕警察。他自己也曾表示,目前最大的壓力其實是來自大眾的輿論。
我認為事件雙方都是結構下的基層弱勢者。公民究責的方向應該指向不思改革的警政高層和制訂移工政策的政府官員,請不要重蹈覆徹誏弱勢者成為代罪羔羊。
最後,還是謝謝各位來看這部電影,雖然這個事件幾乎瓦解了我所相信的台灣價值,但是越來越多台灣公民對《九槍》的支持,讓我再度燃起強烈的信心。
我們每個人都希望成為更好的人,但不應該是踩在別人的身體上前進,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讓台灣成為一個真正民主共好的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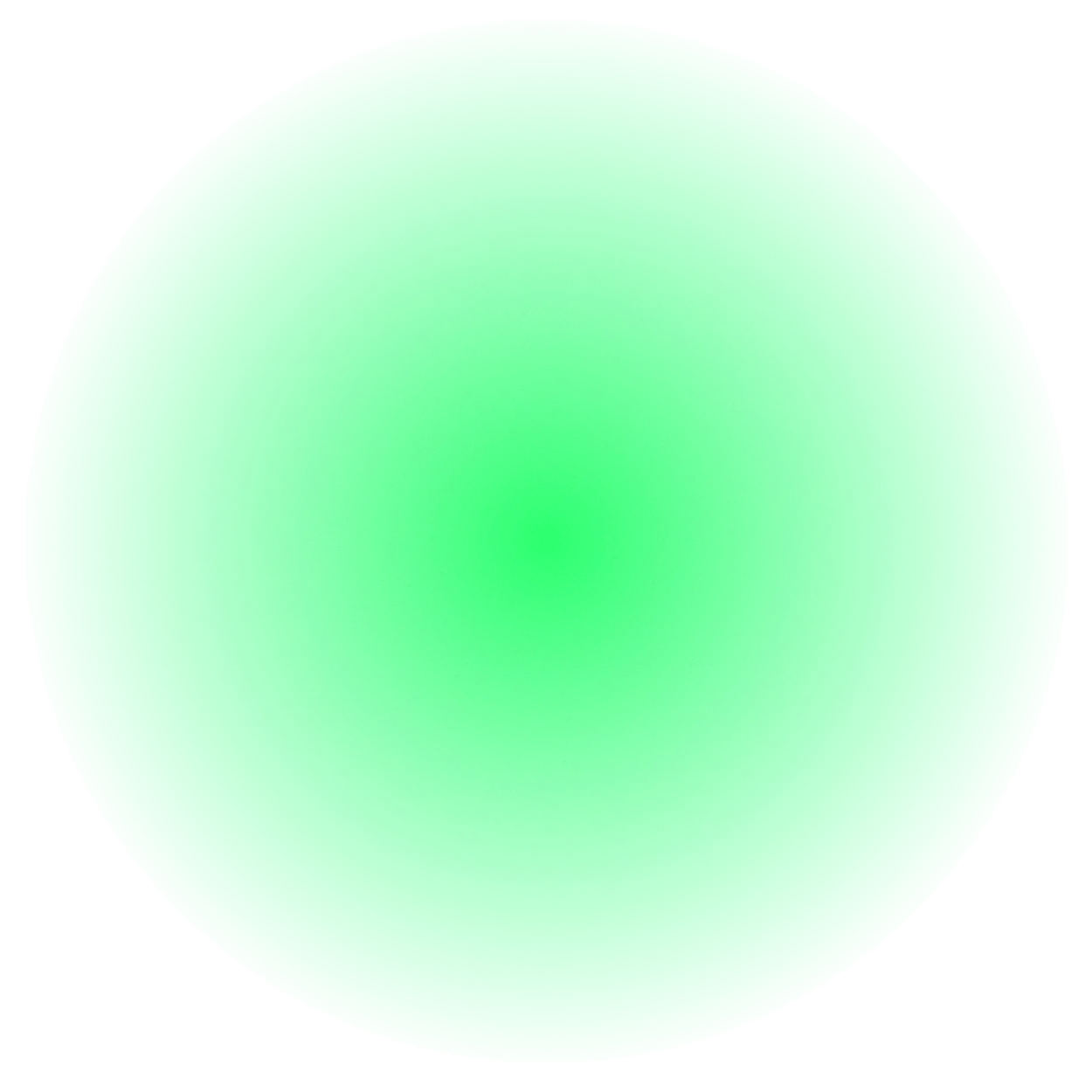
2017年阮國非案發生時,引起社會很大的關注,在爭論的浪潮中,基層員警成為背負九槍責任的代罪羔羊;然而,透過《九槍》,我們思考:「殺死阮國非的,真的只是這9發子彈嗎?」
拍攝這部紀錄片的動機?
以《九槍》的事件而言,被害者和加害者的身份都很清楚,只是加害者是作為臺灣公權力的警察,而受害者是外籍移工。就表面看來,加害者和受害者都很明確,沒什麼好追查的,但由於我們之前做過失聯移工紀錄片,了解到逃跑移工這個問題背後存在很多結構性因素。
所以一方面要查明為什麼他會在那個地點被抓,以及警察開這麼多槍的原因;
另一方面也想藉由此事件的調查讓臺灣大眾更了解:
『為何存在這樣的失聯移工?臺灣有多少失聯移工?為何這些失聯移工今天會走到這一步?』『如同紀錄片中呈現的,一些移工在工廠或宿舍身亡,那麼,是不是只有失聯移工才會有如此遭遇?或是說,在臺灣就連合法移工也隨時面臨莫名死亡的處境?這個事件只是一個個案還是許多結構性因素造成?』
阮國非的事件看似誇張,但其實還有不少誇張的事件並沒有被知曉,《九槍》把誇張的、大家不知道的事件,集合起來呈現在這部紀錄片裡。」
《九槍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片名的由來?
英文片名取自美國詩人 Robert Frost 在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詩中,寫到的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還要趕多少路才能安眠。)
這首詩有兩層意義:休息與死亡。
客死異鄉的阮國非魂魄,來不及回去的家鄉,何時才能安睡呢?
導演 蔡崇隆:「我在念研究所時期讀過佛洛斯特的這首詩,〈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這首詩有一個意境,主角一方面因為體力的關係想回去休息,另一方面是在生命層面上,他似乎不只是想睡覺而已,更接近生命上的死亡。基本上這首詩有這樣的意境,好像一個人很累,卻沒辦法馬上回去睡覺,我身邊有很多移工朋友,基本上都背負人生債務或家庭責任,他們基於那些承諾、責任,沒辦法好好休息。「sleep」也有死亡的意味,一直到他死之前都是背著責任在身上的,其實很多的移工都是這樣。
英文片名直接叫《Nine Shots》的話沒有什麼想像空間,而我認為這首詩反應了我對移工生命狀態的了解,他們很想要回家但回不去,或者是他要回家,但他還有很長的時間他才能夠回去,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休息,我覺得這個意境跟阮國非,或我認識的移工的心境還蠻接近的。
其次就是中正大學傳播系的系主任唐士哲,他英文造詣很好,在想英文片名的時候有跟他討論,是他提出這個建議,後來也採取他的建議,所以才會有這個片名。希望能讓大家看到,阮國非生而為人的面向,其實他就是一個人,一個想要回鄉但是有沉重的責任在身上,而沒辦法回去、沒辦法休息的人。」
片尾曲 Là vì em〈為了妳〉全曲歌詞與由來?
詞 阮國非(節錄自阮國非生前臉書)
曲 史旻玠
唱 賴學靜 林義偉
Là vì em đáng được trân trọng!
因為妳值得被珍惜
Không biết đi trên đường hay đi vô bụi sâu?
不曉得正走在路上,還是已陷入深遂的樹叢。
Đời người là những chuyến đi,
人生中無數的旅程
biết đêm nay đi về đâu?
不知道今晚該往哪裡去?
Bước lang thang... qua từng vỉa hè...
我在人行道上不斷徘徊
Đời người là những chuyến đi,
人生中無數的旅程
không biết đi trên đường hay đi vô bụi sâu?
不曉得正走在路上,還是已陷入深遂的樹叢。
Biết đêm nay đi về đâu?
不知道今晚該往哪裡去?
Bước lang thang... qua từng vỉa hè...
我在人行道上不斷徘徊
Bước lang thang... qua từng vỉa hè...
我在人行道上不斷徘徊
〈為了妳〉歌詞是由《九槍》團隊擷取臉書貼文詞句,交由史旻玠編曲,台越新二代素人賴學靜演唱,聲樂家林義偉合音,以越文聖歌的形式呈現。
密錄器是如何取得的?會不會有法律問題?
導演 蔡崇隆:「我把它拿來放在紀錄片裡面,對我來講某種程度,觀影者是一個社會法庭,我們一起看當時事發的過程是怎麼回事,觀影者是法官的角色,每個人會有自己的心證,法律上來講就是自由心證,你們自己去形成你們的心證。」
法官 陳欽賢:「不會有著作權的問題,因為他沒有原創性,他只是一個記錄,他不是一個創作。比較可能的是洩露國防以外機密,但這個不是機密啊,而且這個讓社會大眾理解其實是跟公共利益有關係的。」
阮國非在身亡前呻吟著,他那時候到底是說了什麼?
為什麼使用「靈魂視角」?如何處理旁白與鏡頭?
移工在臺灣是沒有聲音的人、他們沒有發言權,在這部討論他們命運的紀錄片裡置入移工的角度,在《九槍》中有代表阮國非的視角,我認為非常重要。
阮國非生前,在他剛來到臺灣到過世之間的五年左右,只要他跟朋友出去玩就會留下一些紀錄,或是工作回來也會寫些東西抒發心情,尤其是過世前一兩年的內容,大多都是很累、很難過,或者懷念家人。你會在臉書上看到他所沈浸的心情,這原本只有他的朋友才能看見,我認為這些在生前不被知道的心情,如果在他死後能藉由相關的紀錄片被聽到,也是有意義的。」
《九槍》攝影 詹皓中:「靈魂視角是影片裡有點麻煩、很難詮釋的部分。後來我到越南去,在那個時間裡很密集的跟他的家人相處,靈魂視角其實就是這樣慢慢被建立起來的。知道這個人的個性是什麼,到後面可以從他的朋友(開車的女生)在介紹他,他跟阿非的互動很密切,我就從他的角度去認識這個人,你越認識這個人就會發現他真的就是一個很單純的人。我們一開始可能會看到新聞說他吸毒什麼等等,後來會對他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其實他就是一個很一般的工人,每天付出大量的勞力,然後成為這樣的狀態。在越南那段經驗對我來說很重要,因為我看到他的家鄉,理解到他的生存環境,然後再回到臺灣來。我就會開始從他的角度去看很多跟他一樣處境的人,所以在靈魂視角的拍攝上,會把我自己當成是阿非去拍攝。」
《九槍》攝影 盧盈良:「我們都還活著,無法真的知道靈魂怎麼去看這世界,只能用想像去結構。看到成品後較能理解導演的動機,也很佩服。也許有些人也認為片子相對沒有主述事件或單一主軸,但今天用靈魂視角去串連,因為我們也不知道靈魂何時會飄盪到哪裡去,確實能產生一個不錯的觀影結構。」
為什麼沒有訪問當事者員警?
我不會為了訪問而訪問,除非我想要去突顯這個受訪者,一方面是他的論點有價值,或是他實在太糟糕,讓我想要透過訪問來修理他。但是,他姑姑說的話已經有一定的代表性,我雖然沒辦法認同這種說法,但它還是得在片中呈現出來,因為這個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臺灣主流或中產階級的意見;再者,我也不想修理陳崇文,即使整個事件的槍是他開的,但開槍後的事情經過大家都能在片中看到,不能完全怪他。有經驗的同事跟主管都來了,他們也沒有做什麼處理,也許阮國非本來不會死,所以最後阮國非的死不能完全怪在陳崇文頭上。
如果今天當事者是一個資深警察或者是一個有資源的檢察官法官,我可能會跑去堵他、逼他講,但是這個員警我認為也是弱勢者,一個沒有受到良好訓練的菜鳥警察,即使有那樣的認知也是被培養出來的,他是被養成這樣的。
我如果還特別去訪問他,只是等同於把焦點集中在他身上,讓他變成一個代罪羔羊,但在主流媒體報導下他已經是代罪羔羊了,要不認為他不尊重人權,要不就是移工該死。先前的報導已經是二元對立的狀態了,我不需要重蹈覆徹,這也是我不想訪問陳崇文的主要原因。
我認為這件事情最該道歉的是他的長官們,但他們連處分都沒有,監察院的報告裡面他們都沒有被處分,我比較不平衡的是這個部份。
所以主要是這兩個原因,這是我的取捨,我不想製造二元對立,即使這麼做會蠻好看的,但我不想要為了好看去做這件事。」
有給阮國非家人和當事員警看過這部片嗎?看完的感想是什麼?
阮國非妹妹 阿草:「我跟媽媽說:哥哥的紀錄片完成了,媽媽有想講什麼嗎?她就哭起來了!我們家人希望透過這部紀錄片,讓所有的移工們在他鄉能平安健康,永遠不要再有這樣的案件發生了。我從頭到尾處理哥哥的後事,直到送他的骨灰回越南,所以我很了解哥哥是怎麼死的。
我很愛我哥,但我到不了現場去救他,人家太晚通知我了,如果我可以早點到,哥哥就不會失血太多而往生。
我哥哥的事情,他有對有錯,但不應該是這樣永遠離開。希望政府和臺灣民眾了解我哥哥為什麼落入那種狀況,不需要這樣對移工連開9槍,警方在那個位置是怎麼開槍的,我自己很清楚,很心痛。因為不想讓爸媽拉長痛苦,我當時才決定和解的,讓他們不要一直想。
時間過五年了。目前我在新加坡工作,知道爸媽每天在家平安,我就安心了。我哥是個善良的人,非常疼愛家人和爸媽,如果爸媽看了紀錄片一定會心痛,我想代表他們看就好,因為這是一輩子的傷痛。希望一切都會過去,祝福哥哥在天堂會更好。」